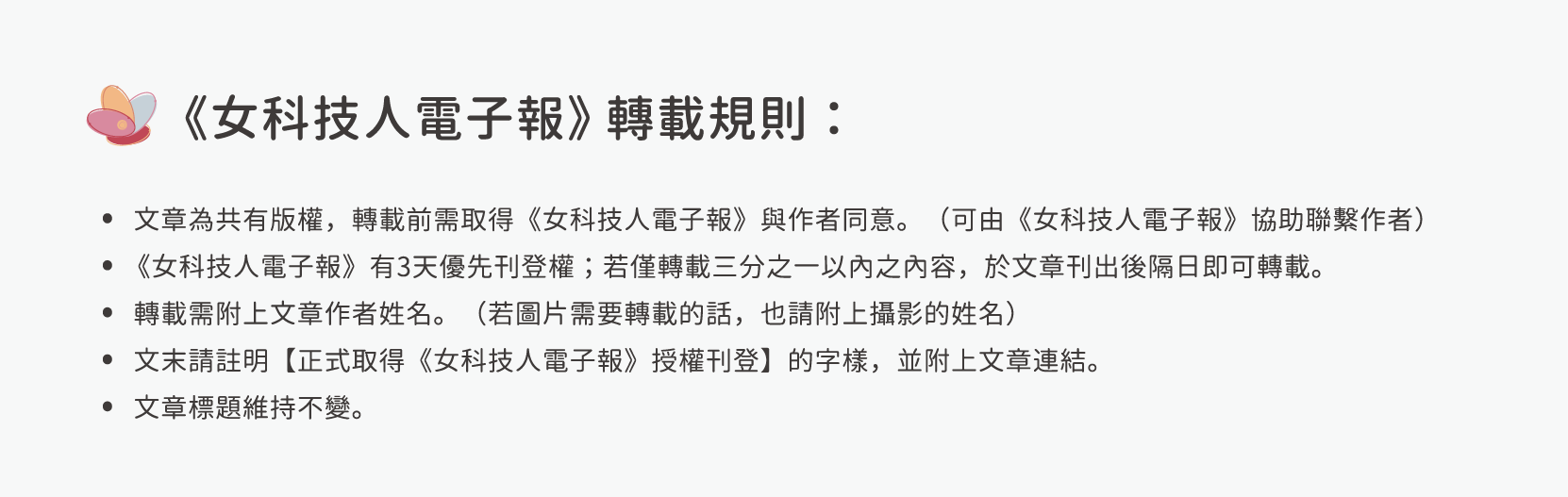※ 作者介紹:Vivian
工作資歷尚未滿五年的Vivian,曾經在政府智庫負責外交工作,在區塊鏈新創開創合作關係,在創投加速器培育新創公司。與此同時,也利用閒暇時間擔任 Girls in Tech Taiwan 的志工,在國內外培育對科技和創業有興趣的女性。在工作中她看見了世界權力中心運作的方式,權力和資源被把持在固定的人手中,機會極度的不平等;而在擔任志工期間,也看見了世界的背面,一群眼神純徹、充滿潛力但卻不被看見的孩子。接下來Vivian即將要自己開始創業,解決看見的機會不平等的問題。本篇文章希望能以這些經歷為鋪墊,最終分享看見的希望。
作者的個人網站:
podcast「 How hard can it be? 到底有多難?」
* * *
20 歲以前的我,怎麼說,雖然生活也還過得去,但總是覺得少了點什麼。我出生在高雄,18 歲以前生活圈就只有鳳山區這麼大(再大也不過 30 萬人口)。國中以前功課還算好,但到了高中之後稱得上出類拔萃的就只有英文這一科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所幸選了語言相關的科系,大學上了德文系,來到了台北。
記得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小時候常看的迪士尼電影《美女與野獸》,開場時女主角貝兒在雜亂的市集中穿梭,村裡的人們對她指指點點,說這女孩雖然漂亮但就是奇怪了點。視角切到貝兒身上,她沈浸在自己閱讀的書中,醉心於書中無限寬廣的世界,抬頭唱道:「我生活的世界不該只有這樣!( There must be more than this provincial life! ) 」
「我的生活不該只有這樣!」簡單的一句歌詞讓電視機前的我愣了幾秒,是啊,難道我的生活就只有這樣的日復一日嗎?我能做什麼?我有什麼機會?我什麼都不知道,似乎只是傻傻的看著日出日落,讓時間不斷地從指縫中溜走。
也許當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時,整個宇宙真的會聯合起來幫助你。無助的我在因緣際會下看到了一段印度童工收容所的影片,我看見和我完全不同的生活,看到不一樣的眼神。透過紀錄片,印度孩子陌生的眼神進入了我的視野,觸動了我腦袋中的某條神經。於是,2015 年初,我決定給將滿 20 歲的自己一份生日禮物 – 一趟到印度童工收容所的旅程。
在印度的故事也許說上 1001 夜都說不完。那時我來到的是一個名為 Mukti Ashlam 的短期收容所,這裡是童工們在警察攻堅被救出工廠後第一個送達的地點,而在收容所的我們也就是他們第一批見到的人類。
這些孩子們的眼神不像我在紀錄片中看見的那樣純澈,而是充滿了防備心的,每一次眨眼似乎都是在記錄潛在危險可能出現的位置。在收容所的日子,我們用肢體語言試著建立人和人之間最基礎的信任感,我們和孩子們變得親近,那是跨越世代、語言和種族的一種親暱感。
有一天,我們請孩子們畫出自己長大後想要成為的樣子。他們四處張望,看者彼此,似乎無法理解我們口中「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這些對話都有請當地翻譯翻成印度文,所以不是語言問題)。我們不懂他們的不懂。為什麼?為什麼這個在我們國小、甚至幼稚園就會被問到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會如此陌生?
一個夥伴提議,我們把社會中常見的一些職業列出來,並且簡單說明這些職業主要的職責,先給孩子們一個框架,再讓他們開始畫畫。於是我們把幾張字卡貼在昏暗的教室黑板前(收容所的教室沒有任何燈泡,只有自然採光),上頭寫著:老師、消防員、太空人、廚師、科學家等等。包羅萬象的職業讓孩子們看得眼花,但也讓他們心裡有了個底,開始畫出 10 分鐘前才開始想像的自己。
在短期收容所中,有一個孩子特別突出,我們說他是收容所的班長。他總是積極地幫我們和孩子們溝通,也總是最負責任地完成每一項交付給他的任務。班長在畫出職業那天顯得格外安靜,他悄悄地坐在位置上,眼神專注,似乎把所有的能量都映在了那張 A4 的圖畫紙上。
課堂即將結束時,我走向班長,問他畫了什麼。他拿起他的圖畫紙,幾乎用炫耀的眼神告訴我:「我要當老師!」為什麼想當老師呢,我問。「因為我不想要其他孩子像我一樣,連自己要做什麼都不知道。」
「連自己要做什麼都不知道。」這些收容所內的孩子們不是不想想像自己的未來,他們根本不得其門而入。他們不是不敢作夢,他們是連「夢是什麼、如何作夢」都一點概念也沒有。在孩子們知道世界上有太空人之前,他們怎麼可能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個太空人。
紐約城市大學研究中心哲學教授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知識的不正義》一書中曾提過一個概念,叫做「詮釋不正義」,代表在集體認知的差異下,部分族群受到的苦無法被詮釋,因為世界根本還沒有這樣的詞語來詮釋。其中一個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在「性騷擾」這個詞被廣泛認定且運用以前,沒有女生知道要怎麼形容自己每天在生活和職場中遇到的困擾,這些困擾看似微小,但卻深深的影響著被騷擾者的日常,甚至自尊。
印度的孩子們沒有機會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受限於狹隘且受操控的世界觀,他們沒有機會受到最基礎的教育,更遑論發展出自己對未來的想像。在他們的世界裡,他們沒有辦法充分的詮釋自己的想望,因為他們不敢想、沒想過要想、或根本不知道能怎麼開始想。我把這樣的不正義稱為「機會的詮釋不正義」或是「未來的詮釋不正義」,如果所有的超越日常想像的機會對這些孩子來說都只是他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他們更是沒有機會跳脫不斷被複製的階級和人生。
後來我發現了,原來我和印度孩子們高度的連結不只來自我的同理心 ( Empathy ),更多是我的自我投射 ( Projection )。儘管我的出生相對優渥,並且有機會完成義務教育,甚至進入到高等教育體系。但從小各種刻板印象、限制信念和環境中有限的資源,在在侷限了我對自己的想像。我以為讀完語言科系的我就只能當個翻譯或是空服員,我想都沒想過自己有其他可能,或是自己有能力為自己創造不同的機會。
我很努力,也很幸運,離開印度之後我確定了自己對人權議題的興趣。我進入婦女人權相關的基金會實習,在不同的社福單位擔任志工。後來將語言能力和對人權的興趣結合,展開了一段外交工作的生涯。這接二連三的機會,對我來說就像是用盡全力突破一座又一座的高牆。我不再是住在洞穴中的囚徒,我把原本被藏著掖著的世界一層層剝開,步履之間仍帶著恐懼,但卻也興奮無比。
對於人權的興趣後來帶著我進入了一間區塊鏈新創公司,我開始將網路世界中的數位人權視為己任,工作中更看清楚科技如何加速「機會的詮釋不正義」。在相對優渥環境出生的孩子們,現在無一不從小學習程式語言,彷彿他們從小就站在聖母峰的山頂,俯瞰這世界的所有可能性。
而那些相對弱勢的孩子們呢?如果他們連傳統的教育體系都無法進入,他們要怎麼有機會學習這些新興的技術,又要怎麼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未來?如果說程式語言就是下個世紀的通用語言,這些孩子將失去他們本來就所剩無幾的話語權,讓「機會的詮釋不正義」催化階級複製,過上似乎難以被翻轉的人生。
在厭世代中迷惘的我們就像這群相對弱勢的孩子(某種程度上啦),我們在制式的教育環境中長大,一不小心就陷入了「機會的詮釋不正義」。現有的教育體系似乎沒有能力教會我們充分思考、看見機會、探索未來的機會,我們被既有的框架束縛,找不到自己的價值,也就此認定自己沒有價值。
我很努力,也很幸運。我幸運地瞥見了洞穴外的機會,並且努力往機會邁進。我幸運地認識了一些改變我思考方式的人,並且努力地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我還在學習的路上,學習如何學習、學習如何思考、學習如何找到自己。我相信我的努力和幸運是能被複製的,我相信「機會的詮釋不正義」可以被系統性地打破,我也相信每一個個人都有機會把世界形塑成更好的樣子。
離開區塊鏈新創的我下定決心要自己創業,我要用我對人權、科技和權力結構的理解打破更多「機會的詮釋不正義」。我還在路上,路還很長,但至少我知道自己可以踏上這條路,並且有能力想像這條路即將帶我走向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