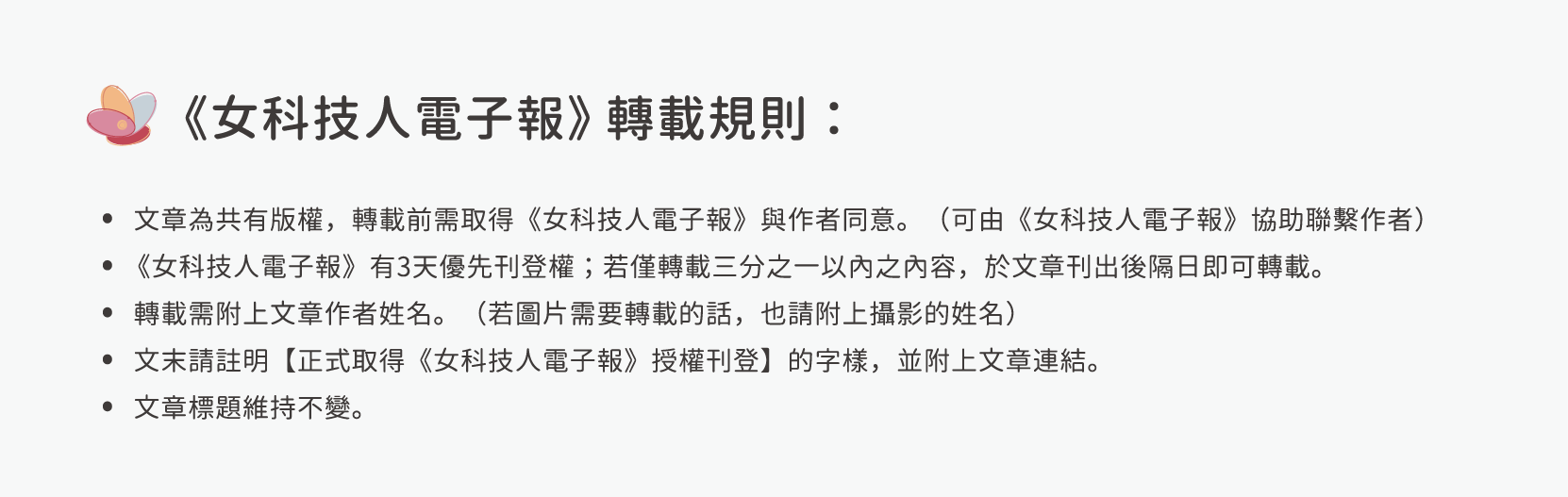一條看似與部落疏離的路
「喂,您好!是Panay vuvu嗎?我是部落健康營造中心的專案經理。」我向電話另一端的部落長者介紹我自己,對方疑惑著問我:「是哪一個營造公司嗎?」我笑著跟長輩介紹我的工作。
咚咚咚咚,是鐵鎚敲打鐵釘進入模板的聲音,是工地的聲音,一起工作的部落大哥笑稱我們是「生命的鼓手」。是的,我的職涯就從一個建築工地的模板開始。我是一位原住民族青年,成長於台東部落中這片美麗的土地。這裡的每一棵樹、每一條溪流,都是部落的延伸;獵人從山裡帶回豐收的獵物,老人用木杆打著小米,孩子們在空地上追逐歡笑。但時代的快速變遷,部落遷離了山林,獵場成了禁區,年輕人不得不收拾行囊,背負著思念,走向那座陌生的城市。部落留下了老人與小孩,我們的父親去遠洋成了遠洋漁工,大哥哥們到都市去從事建築工作。從學校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我選擇了一條看似與部落疏離的路:成為都市建築工地上的模板工人。
在那些沉重的日子裡,我的身體感受到了無情的勞動壓力,背部的酸痛與手指的繭子成了生活的證據。但同時,我也從同事們的笑語中,感受到了一種微妙的連結。許多人,和我一樣,來自原鄉,他們,帶著「為家庭而拚命」的使命感,而我卻對工地生活感到茫然。對當時的我來說「搬一塊模板,就像是在堆砌一段陌生的生活。」工地是一個「3D」的世界——危險(Dangerous)、骯髒(Dirty)、困難(Difficult),卻是我們僅剩的選擇。
在工地上,我學會了傾聽,學會了觀察人的身體如何與生活抗爭。那些疲憊的臉龐告訴我,健康並不只是醫院的診斷結果,而是能否有力量站穩在生活裡,能否在苦難中仍保有希望。這段經歷,讓我對健康的理解開始變得立體:健康不僅是醫學名詞,更是能否穩定地生活與愛護身邊人的能力。
身體裡,土地的靈和族群的魂
離開工地後,我決定回到部落。雖然山林的沉默讓人心痛,但文化的聲音依舊在。我有機會成為學校原住民族舞蹈社團的老師,透過舞步與音樂,試著讓年輕人重新感受到自己的根。在教導學生傳統舞蹈時,我重新連結了自己與族群的深層記憶。每一個舞步的揚起,都讓我感受到祖先的故事在重生。我告訴學生們,跳舞時,不只是動作的重複,而是讓土地、語言與族群的靈魂透過身體說話。某一次,社團中的一名學生告訴我,他因為舞蹈找回了對自己族群身份的自信。那一刻,我開始明白,文化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深層的療癒力量;我深刻體認,文化是重建健康的一種方式。它療癒的不只是身體,而是心靈深處的自我價值感。
我也擔任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志工,創傷總是來得那麼深重:失去親人的痛苦、生活壓力的折磨,還有那些從未被治癒的舊傷。一名案主告訴我,他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回到正常生活」。他的話讓我想起部落中因失業而陷入酗酒的朋友,也讓我想起自己在工地時孤獨無助的夜晚。我只能靜靜陪伴他,因為我知道,有時候,陪伴本身就是一種療癒—它讓人感受到,儘管世界多麼殘酷,他仍然不是孤單的。
零散後的交織
如今,我身為部落健康營造專案經理人,扮演的角色不僅是規劃者,更是文化與健康之間的橋樑。我將自身的職涯經歷編織進工作中,試圖找到部落文化健康的獨特語言:
我從工地學到的,是尊重每一雙勞動的手。我特別關注部落勞動者的健康問題,推動勞動傷害預防計畫,讓族人能以更安全、更健康的方式工作。
我利用舞蹈的經驗,設計出富有文化意涵的健康活動,例如長者的手工藝療癒課程或青少年的傳統體能挑戰,讓文化成為心理與身體療癒的策略,也讓文化成為我們面對現代困境的力量。
從志工的經驗中,我知道每個人的痛苦背後都有一個孤單的故事;在志工經驗中學到的同理心,讓我更能傾聽族人深層的需求。我強調部落社區的互助性,例如長者與青少年彼此支持的計畫,重新編織一個健康的社會網絡。
我的職涯經歷看似零散,但其實每一段都像是一根線,彼此交織成了現在的模樣。工地的汗水、舞台的旋律、陪伴的沉默,這些經歷讓我看見,健康並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整體的、深深嵌入文化與關係中的過程。每一次與族人的交流,每一次看到他們的笑容,我都更堅信這條路的意義。健康,不僅是存活,而是活得有尊嚴、有文化、有彼此。
山霧升起,陽光灑在部落的山間。我抬頭望向天空,內心有一份平靜。這條路,或許並不容易,但我知道,它是屬於我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