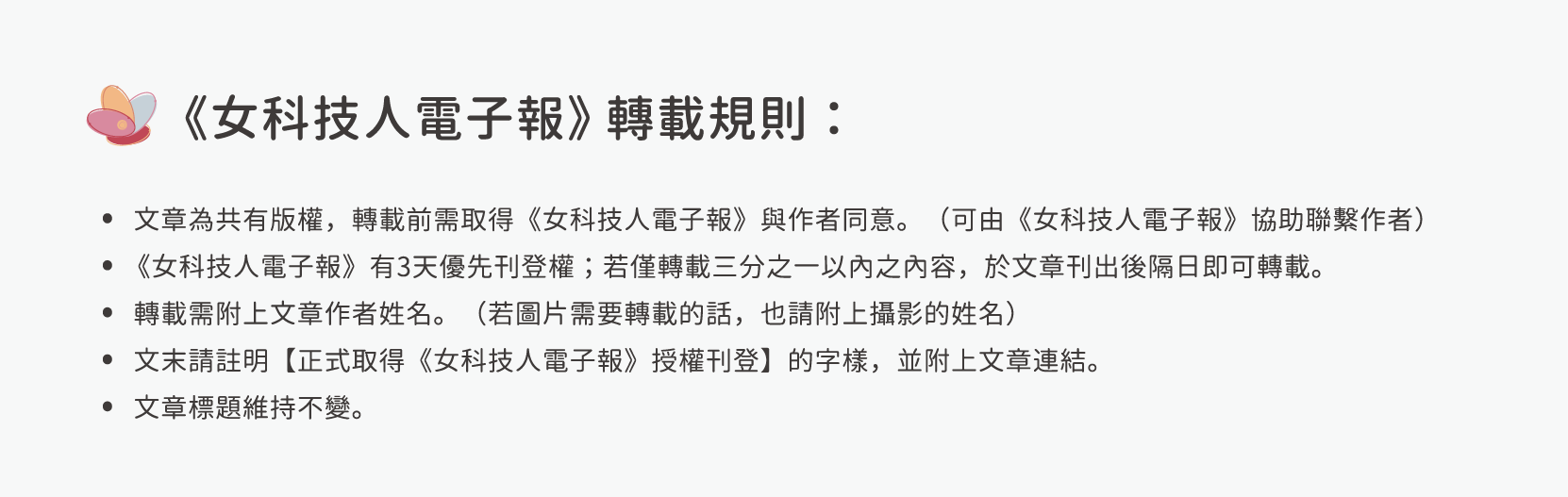我的生涯可能很不一樣。第一在求學和教書過程,我待過除了醫學院以外的所有學院,因為都市計畫是跨領域的專業,在不同的學院都有它的用處。第二是在美國留學,畢業後先回台灣教書十年之後又回美國教書,因為在美國和台灣的學術圈都待過,所以有很多體驗。
換學院、換國家,最神奇的是我教的課都一樣,研究也一樣。關心點也沒有太多改變:不平等、全球化有關的政治經濟變遷,像是新自由主義化和新近興起的金融化。到美國的最大改變是台灣意識的覺醒,關心台灣怎樣在中國崛起時,如何被美國學院定位和解釋,台灣的議題也變成最憂心忡忡的問題。
之所有這樣的適應力,可能跟我一直都在非主流的生長環境有關。我在嘉義鄉下長大,上小學才開始學國語。鄉下小孩的成長就是離家愈來愈遠。從小學一路到美國念研究所,每換一個階段,就換新一批同學,所以很習慣自己邊緣的位置,習慣從陌生到熟悉,永遠在學舌講標準非母語。
性別意識發展跟原生家庭有關,我媽媽只有小學畢業,但在小時候,我媽媽是竹崎最厲害的三個女人之一,因為她是村子裡第一個會開車的婦女,加上很會做生意,很多男人會做的粗活她都會做,所以我長大時沒有甚麼性別的框架,直到高中選理工組時,才發現理工的女生是高中的少數。
性別的差別待遇是到大學才清楚感受到,處於工學院的少數,這經驗很多科技界的姊妹都有提到。因此當台大女研社成立時,很快就參加,也在這裡找到很多支持的力量。性別也是我看世界的一個角度,回台灣工作那十年,一直在邊緣的學術環境掙扎,無法將很多性別和都市空間的議題推入主流的都市計畫教育和實踐之中,之後到許多國家看到很多以婦女需求為主的都市計畫,覺得以前無力在台灣推動有點可惜。幸好在社會住宅推動時,可以透過寫作和參與討論的方式,提供建議,所以現在社會住宅有育兒和養老的設施,還是覺得很欣慰。
都市計畫和其他社會科學最大不同是,都市計畫的想法最後都會變成實質的都市和居住空間,這些實質的空間就是最具體的社會資源,也是很多社會關係形成的和發生的場域。這些實質的空間是我們仰賴維生的基礎,例如住宅、交通、馬路。現在都更豪宅漸漸成為都市的地景,非常令人擔心,因為台灣從沒有討論過都市要長成甚麼樣子,現在擁擠的高樓漸漸取代舊有的低樓層都市,一個個蓋滿滿的方塊建築,把容積率用盡,高樓變成新的貧富垂直隔離的方式,住宅一直被當成商品遠重於居住的家屋,整個學界和實務界沒有太多反省和足夠的力量去抵擋。
我回台灣時,助理教授的階級剛被設立,大學也建立三分之二的條款,新聘老師必須要超過三分之二的投票同意,那時SSCI也開始設立。當時非常奇怪的現象是很多系所的所有老師沒有人有一篇SSCI論文,但卻要求新聘的老師必須要有一篇。不過還算幸運,因為台灣普設大學,還有很多學校可以去。
但是新設的大學一切未上軌道,從南華大學換到花蓮教育學院,被師專體系壓榨新人的文化震撼到,尤其是新聘老師義務行政兩年。都市相關領域派系林立,各個派系築起高牆在裡面自我生產,無法對話,最糟糕的是這個領域訓練了所有塑造都市的官僚和業者,這也解釋台灣的都市問題大部分都無解的原因。
我在台灣浪費寶貴的十年。之後去了很多國家,看他們怎樣培養學術人才,所以一直主張台灣各級政府或大學應該廣設研發機構,因為整個政策研發的機構非常的少,政策應有的數據和調查非常粗糙和貧脊,社會還是停留在期待另一個蔣經國、李國鼎復活的思維,認為只要有強人的領導就會有好的政策,而不知道政策的擬訂在民主化的社會,需要更多的知識基礎和社會參與的過程。在我之後有更多優秀的博士生失業,新聞只把博士賣雞排當成幸災樂禍的笑話,而不知道珍惜人才、培養人才,自廢武功很可惜。
回到美國重新開始很辛苦,不過美國學院有比較多培養新人的文化,而且升等的條件清楚,新進教授一開始減授時數,加上教學輔導的體系,派兩位教學優良的老師當師傅,所以在升等之前,專心在教書和寫論文上面,人際關係單純,辦公室和居住環境優美,是一個可以很專注工作的環境。剛開始教書衝擊很大,因為這裡的師生關係和台灣非常不同。在台灣教書需要在課外花很多時間和學生相處,上課的內容其實不多。美國的教書比較是契約關係,光是教學大綱的寫作就非常不同,怎樣評分、每次上課內容、各種上課的規定和期望,都必須非常小心和仔細。適應的過程一直在摸索怎樣和當地的文化連結,現在待過超過十年,新進學生又是新的世代,也必須因應調整教學方式。在這裡沒有靠山,完全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