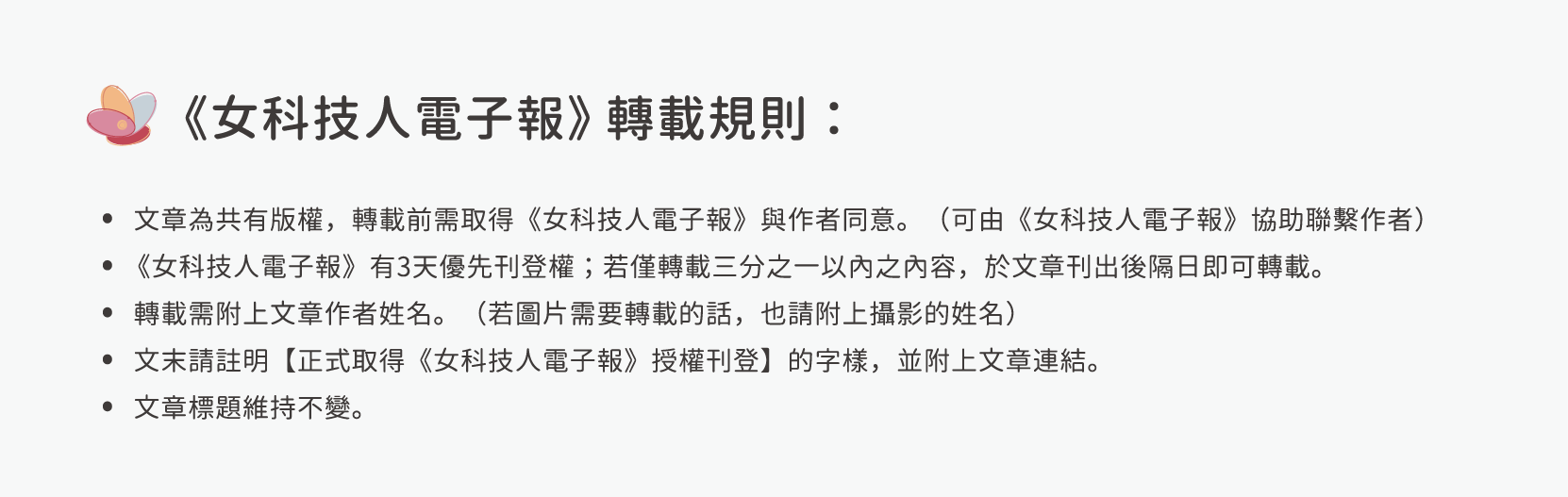二十多年前,一位剛從某國立大學畢業的女性進入一家資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部門氣氛輕鬆融洽,同事們感情很好,但他卻覺得格格不入:身為辦公室唯一的女性,其他同事們從不停止的黃腔讓他難以忍受。當時性別平等工作法尚未立法,對於辦公室中的性別議題和人際互動幾乎沒有規範,他鼓起勇氣向直屬長官反應,出乎他的意料,這位長官非常支持他,要求部門同事都不可以有開黃腔、讓他人不舒服的言行出現。
只是更沒想到的是,此令一出,部門同事大反彈,認為主管偏袒,無視其他同事在工作中的紓壓需求,因此這些同事不說黃色笑話了,但有一大批人,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同時擺出清涼泳裝照。這位女工程師和他的主管當然注意到這件事,但當他們提出質疑時,這些工程師的回答是:「難道我們連辦公桌的擺設自由都沒有嗎?」之後日常生活中的酸言酸語當然不會少,還加上一些若有似無的排擠,最後這位女工程師離職了,離職前主管跟他說:「很抱歉最終我還是無法保護你。」
三年前,一位在科技公司總務部門工作的朋友來諮詢性騷擾申訴事宜。公司茶水間的咖啡、零食等的準備工作由他負責,某天他帶著工讀生去整理,裡面剛好有兩位他認識的同事在煮咖啡,他隨口招呼:「可以加奶喔。」其中一位男同事盯著他的胸部,帶著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說:「用你的奶就好了啊。」兩位男性發出他認為「聽起來很噁心的」笑聲。
剛放完產假、還在哺乳期的他深感屈辱,因此決定申訴。他本來以為有物證(監視器畫面)人證(工讀生),申訴不成問題,沒想到調查委員採信對方辯稱「我是在說他準備的奶精球」,並以「監視器沒有錄到聲音,無法證明兩人是否有發出笑聲」為由,判定性騷擾不成立,當事人在申覆失敗後決定辭職。
在十一月女科技人學會和不小盟合作的線上演講前,我跟這兩位朋友聯絡,想知道經過這段時間,他們現在的想法。第一位女工程師現在是某金融公司的資訊部門中高階主管,他說:「或許我該『感謝』他們?謝謝他們讓我認知到自己無法在性別比例失衡的環境工作,所以從那個公司離職後,我就轉換跑道,只找非科技業資訊部門的工作。或許繼續留在科技業,我不會有現在的成就。」第二位女總務則轉往其他科技業公司的庶務部門工作,他說他對同事刻意更疏離而不信任了:「留在科技業是我們這種文組科系能找到薪資較高的產業,我把在公司中這種『工程師和其他人』的隱形階級、隨時武裝自己以面對可能同事不經意就會說出他自認沒問題但事實上很冒犯的話、這輩子可能沒什麼升遷機會,都當作代價,是我基於家庭經濟需求所需要付出的犧牲。」
我又問他們:「會對跟主管反應╱提出申訴感到後悔嗎?」擔任總務工作的朋友說:「是不會後悔,但如果再來一次,我可能會選擇直接辭職。知道自己沒有錯卻被權力壓制才是最傷人的,既然最後都是離職那不如少受一點來自其他人的傷害。」我問:「但沒有申訴也是會不甘心吧?」他沉默了一下,說:「是,會變成現在是為了沒有申訴而後悔。這件事對我傷害真的很大,那段時間我哺乳時都在哭,因為會一直想起對方的口氣和眼神。」
自己也成為主管的工程師朋友回答更複雜。他說:「經過這麼多年,已經不是後不後悔的問題。在那當下當然很受傷,但我那時很年輕,職位很基層,離開一個不愉快的職場要付出的代價比起現在來說很小。而且我當上主管後,這個經驗反而讓我懂得要注意辦公室細微的權力關係,對於冒犯言詞有更高的敏感度,多照顧一些比較邊緣的同事。我那時會反應不是因為是非對錯,是因為天真地相信主管會照顧我。」我問:「但當年的主管確實有照顧啊!」他說:「太慢了,當辦公室文化已經形成,就不是你單向的主管要求可以改變。不是有人被傷害才開始處理已經扭曲的辦公室文化,而是一開始主管就要思考清楚這個辦公室要怎樣的氛圍。」
這兩個故事,即使橫跨二十餘年,性別平等工作法從無到有,但結局卻是一樣的:受傷害的人都離開了,而且都用「轉念」的方式處理他們的經歷。從積極面來說,這樣的經驗造就一個更體貼的主管,或更知道「工作」在其生活中扮演怎樣定位的個人,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可能是「倖存者偏誤」:那些飽受身心困擾、再也無法恢復、就此離開職場的受害者呢?
性別平等工作法在2023年最近的一次修法中,大幅增加並明訂對雇主的要求,除了明訂雇主為行為人時的處理方式外,更多的是推著雇主或主管去思考,怎樣去創造一個人人可以安心、專心工作的場域?而校園中正式的性別平等教育也已進行二十餘年,我們養出怎樣的公民,在日常生活當中表現出怎樣的性別態度,恐怕才是形塑「性別平等╱友善職場」的核心議題。
在數量上性別比例常常失衡的科技現場,可能需要在其中的人更細緻地「看穿」這些隱形規則,並且從自己做出改變;不再將對方的「不舒服」輕易歸咎於個人「太敏感」或「破壞氣氛」,而是願意重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互動模式,是否隱含了將特定群體排除在外的敵意。唯有當尊重成為無需刻意提醒的日常,我們才能真正終結這二十年來不斷重複的「離開」輪迴,讓職場成為所有人都能安心發揮專業的所在,而非必須隨時武裝自己的戰場。